少年强则国强,少年的你却受伤

1
知乎提问:校园欺凌到底有多严重?不就是互相打来打去的吗?说到心理伤害,现在也早就痊愈了啊,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小题大做?
高赞回答:站在桥上的人不会明白桥底溺水的人有多痛苦。
从《悲伤逆流成河》到《少年的你》,校园欺凌终于走入了人们的视野。之所以说是“终于”,因为我也是上大学以后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曾经遭遇的是校园欺凌。
审视现在的自己,虽不至于像作品中易遥、陈念那么惨烈,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价,但成人形态的自己却始终被曾经校园欺凌的阴影所笼罩。这些经历好似完好皮肤下若隐若现的胎记,一旦暴露在炙热的阳光之下就清晰无比。
之所以撕开结痂的伤疤,一则是希望当年的坏人们有机会得见的话,有机会做个好人,而不是长大的坏人;二则是希望给正在遭受校园欺凌的同学些许温暖,请你放心去保护世界,我会尽力保护你。
前段时间一个女童的眼睛里被塞纸片的新闻沸沸扬扬,让我想起了幼儿园时期这段经历。那时候年纪尚幼,我的记忆已经比较模糊了,部分是我父母后来告诉我的。

2
某天放学回家后,爸妈发现我的鼻孔里面黑乎乎的,于是父亲拿来了镊子,把我鼻孔里的东西一点一点夹了出来,里面都是混着鼻血的卷成小卷的吹塑纸。平日里我的记性还算不错,但是这一天真的像失忆了一样,只依稀记得下午是和一个姓莫的女同学一起玩耍。后来好像发生了一些不甚愉快的事情。我父母气急之下找到了那个女同学和她的家长,她也承认了往我鼻孔里塞纸的事情,不过原因就只是说“好玩而已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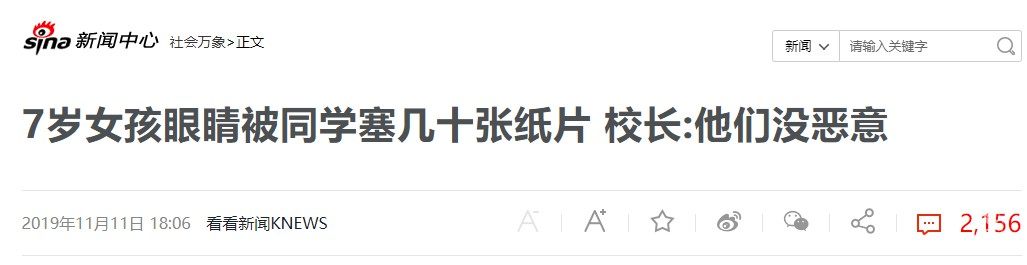
在厂矿小学读书时候,我是一个满脸是雀斑的小姑娘。大约三、四年级,班里有一个男孩子一直取笑我,并且伙同班里的其他同学一起欺负我。心思细腻的我经常为此偷偷地哭。这种情况影响了我差不多一个学期,原本性格很开朗的我变得很抑郁。我爸妈已经劝了我很多次,说是不要放在心上。换成现在的我大概能够释怀,但是对于当时小小的我而言,这一点悲伤足以充溢我小小的身体。后来还是我爸用特别男人的方式找了那个男同学,口头明确警告了他,后来这个男孩子再也没有欺负过我了。感谢我的爸妈一直在背后支持我,否则我也许和许多的易遥、陈念一样孤立无援了。
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保持强硬的重要性。一个下午的放学,我负责打扫卫生所以最后一个离开班级。班里的调皮的男生君君(化名)把我拦在了教室里不准我出门,这样僵持了快一刻钟,我尝试着跑后门、大声援救都没有用,他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出门。眼见天色渐暮,我变得害怕起来,这时候我想起我爸告诉我“有时候忍耐和软弱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,你要学会“雄起”(重庆话,意为和挑衅者干上一仗)”。当时的心理状态都还记忆深刻,我鼓起勇气走到他跟前,扇了他一耳光,然后飞奔到了老师办公室,把门锁上后呼吸久久不能平复。后来君君也没有再追上来,我过了一段胆战心惊的日子害怕他报复,所幸生活归于平静。
六年级时候转学去了区里最好的小学,班主任是一位李姓语文老师,她让我和班里最差最调皮的学生长长(化名)和翔翔(化名)分别做了一个学期的同桌。到了新环境,敏感如我能感觉到班里的女生们有一个我进不去的小团体,班里的男生在背后对我不那么好看的脸议论纷纷。于是开始习得小心翼翼,直到翔翔丢了五元钱,不阴不阳地污蔑我偷钱。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情是如何收场了,只记得被别人污蔑的委屈和瑟瑟发抖的我。直到我长大成人,无意中认识了那两位男同学的母亲,谈及她们的儿子两位母亲都觉得很乖巧且并无恶习。
是的,留在别人身上的污水怎么能算自己的恶习呢?
六年级下学期,有一次晚上妈妈去开家长会,有一个叫柳树(化名)的小姑娘守在教室里向我妈妈诬告说我打人,打一个叫杨树(化名)的个子小小的男孩子。我不知道一个12岁的小姑娘为什么要杜撰这样的故事,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将她自己打人的情节安在我的头上,只知道回家以后妈妈把这个事情转述给我听,她没有表达对我的信任,也没有表达对我的质询。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人性的可怕之处在于没有人百分之百的信任你,也让我第一次有了念头:“如若有人对我无条件信赖,那我一定不可以辜负,因为这种信任太珍贵了。”
终于进入了初中,这是兵荒马乱的三年。这个班级里面是全区成绩最优秀的学生,他们中有人后来考上了清华北大,有人后来成了了中科大的博士。可是于我而言,只记得把我饭盒藏在窗帘里的坏人,把我凳子螺丝拧松让我摔跤的人,把水盆放在门梁上让我在大冬天湿漉漉的人,用重重的拳头锤我把我推倒在地的人。愤怒掀过桌子,吵过喋喋不休,沉默假装臣服,似乎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解救已经深陷于泥泞中的我。可以把你的愤怒当做笑话,把你反抗的语言当做谈资,把你的示弱当做理所当然,生活陷入了寂静。因此我特别理解易遥投水的那一个慢镜头:全世界终于安静了,终于不是四面埋伏,终于不必腹背受敌,终于可以敞开心胸拥抱这个世界,哪怕是最后一次。

文字解救了我。如果说一开始对文字的喜爱源自对生活的感慨,那么初中的我已然把文字当做了情绪的倾斜口。我开始拼命地写,所有的开心愤怒悲伤满足都在文字里面。可是文字也未必是安全的,因为你的周记本、日记本都会被人偷偷打开,你的心迹会被人拿出来诵读。在现实处境最难捱的时期,我不敢一个人骑车放学,因为会有人骑车在后面追我,让我觉得自己是被围猎的猎物,一不小心就会像金枝一样踩到人生的捕兽夹子。我试着向老师求救:班主任老师是教数学的,我数学向来不好,他对我也没有什么好感,毕竟对我意见特别大的那一群人都是数学很好的尖子生;语文老师同意放学的时候捎带我一起,于是我那半个学期都是跟着我的语文老师走的,至少老师在,这群初中生们还不能那样肆无忌惮。
记得有一次体育课,老师让自由活动,被孤立的我只能在操场上闲逛。这时我们班的一位成绩很好的女同学走到我跟前,问我:“这样生活,很艰难吧?”那一瞬间我泪如雨下,虽然我和她当时并没有过硬的交情,但那一瞬间让我感受到了懂得。
读到高中,我好像终于掌握了一些避开欺凌的方法——保持沉默,绝对的沉默。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就不会被别人欺凌,这好像是唯一一种让自己待在安全区的方式。所以我开始变成了沉默寡言的那个人,纵是内心奔腾浪涌表面也要波澜不惊,这样的经历让我过早地变成了一个成年人。
到了大学,慢慢长大的我雀斑没了,可是放纵的大学生涯使我长肉。而同龄人的审美从只看脸变成了看身材,我又中枪了。嘴欠的男同学恨不得忽略自己200斤的肥壮身体也要嗤笑你165cm、60kg,而且一说就是四年。不过这四年我开始接触到带我走出阴霾的人,开始有人愿意和我一起面对那些恶心的话,开始有人代替我的父母帮我回击这些肮脏的东西。脱胎换骨是一瞬间的东西,大学毕业的一瞬间我感到的释放与解放,那些不愉快都留在了校园里寝室里,生活逐渐有了起色。工作后又读了研,遇见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,彼此的关系是成年人的交往方式。不会过多干涉生活,但是又彼此关心一起进步。那一瞬间我回望我的前面近二十年时光,浑身轻松,这一次,是真的可以离开了。岁月对于我而言,真的是带来了馈赠:十几岁时不知道怎么打理的发型和皮肤,精心自我管理的身材,一次次试错中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穿衣风格。
记得有人告诉我,经历过校园欺凌的人很难走出来,但可以在文学作品里好好哭一场。走出地狱后的遗留正是对自己的过度保护所产生的易怒和过于敏感,我只能安慰自己把这种敏感作为一种天赋,每天内心独白都有几万字的我,几乎所有的碰撞,内心都会有回响。影视作品里面的很多女孩子都是“全然单纯”的被动女主,而我不是。我会抗争,我抗争的路上也并非无一人关怀我,我的故事很复杂。易遥有顾森西,陈念有小北,虽然我的故事不如文学作品一样向死而生,但是我感谢这段路上带我一段的每一个人。
感谢我的父母,他们明智且伟大;
感谢初中的语文老师刘老师;
感谢一路上爱过我的你们,爱真的可以拯救绝望。
如果你正在遭遇校园欺凌,我愿意保护你。
关于我们
筷子小手是一个介绍重庆小众吃喝玩乐的神秘组织,欢迎关注我们,我们记录了旅途中有趣的瞬间,就等你来发现😀